大評論家 | 時間的複調書寫 | 大館河原溫個展 | 自由之律,律之自由
- experience am space

- 6月15日
- 讀畢需時 10 分鐘

當社交媒體將人類的存在壓縮成九宮格裡的像素碎片,香港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展廳卻在紙頁的摩挲聲中展開了一場關於 「存在」 的逆向敘事。作為全球首個河原溫(On Kawara)逝世後策劃的機構個展,這次展覽是藝術家逝世10年內不辦大型展覽的遺囑解封後首次全面展示其50年的創作全貌。「河原溫:自由之律,律之自由」(2025年5月23日至8月17日)在 2025 年春夏之交構建起一個穿越時空的場域,由侯瀚如和郭瑛共同策展 —— 這裡既是對概念藝術先驅的深情致敬,更是大館作為文化樞紐對 「印刷媒介如何承載人類經驗」 的當代性重釋。
✍️加入我們「大評論家計畫」,詳情:https://www.artmap.com.hk/main-page-junior-art-reviewer


| 漂泊者的時間詩學:河原溫的創作軌跡與概念藝術的共振
策展人侯瀚如以其與河原溫逾三十年的深厚情誼為線索——自90年代在上海當代藝術館相識,並作為百萬年基金會(One Million Years Foundation)成員與藝術家董事會成員,侯瀚如不僅是河原溫藝術理念的見證者,更通過此次大型回顧展,將藝術家橫跨半世紀的創作實踐轉化為關於「存在」的跨時空對話。
河原溫出生於1932年12月24日,在2014年在紐約離世,他的藝術生涯本身即是一部流動的地緣志。他生於日本刈谷市,1951年移居東京後成為戰後前衛藝術核心成員,1959年赴墨西哥城研習現代藝術,1962年起輾轉紐約與巴黎,最終定居紐約卻保持全球遊牧創作。跨越文化地理的遷徙,使其作品天然攜帶「全球公民」的視角,成為個體存在與集體歷史的交匯點。

作為概念藝術的關鍵人物,河原溫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最早純粹以概念(記錄時間、存在)為核心進行創作的藝術家之一。他的創作始終與紐約興起的觀念運動形成呼應又保持疏離。河原溫突破了傳統畫布的框架,對後來的概念藝術運動影響深遠。作為概念藝術先驅,其創作核心在於「通過自設規則實現精神自由」。他拒絕傳統藝術表達,轉而以極簡的日常記錄存在。

概念藝術通常借助語言工具進行創作,其關注點在於想法本身,而非形式。當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以「觀念藝術論」強調「概念高於製作」,勞倫斯·韋納(Lawrence Weiner)以文字宣言消解視覺霸權,同期概念藝術家們剝離藝術中的個人情感,將其簡化為近乎純粹的資訊或想法,並大大淡化了藝術對象本身。當他們沉迷於理論建構時,河原溫卻選擇用另一種「語言」,近乎苦行的日常儀式——每日繪製「日期繪畫」、寄出《我起床》明信片、記錄《我去過》的地圖,將個體生命轉化為可觸摸的物質記號。這種「去情感化」和對「時間在場性」的記錄方式,恰與概念藝術「觀念高於形式」的核心理念形成互文,既遵循概念藝術「去物質化」原則,又以手工痕跡的溫度顛覆了流派常有的冷漠疏離。
侯瀚如曾提及,河原溫「從不用理論框架束縛創作」,其靈感常源於餐廳報紙剪貼、當地語言書寫,這種將哲學思考熔鑄於微小日常的方式,恰與杜尚「現成品」理念形成跨代對話,卻更具存在主義的沉鬱質地,也被後世稱「藝術家中的藝術家」。
| 河原溫的特殊性:在規則與自由的辯論
河原溫畢生致力於以基於語言和數字的藝術探索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系列作品,以存在主義和冥想的方式記錄他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活動。
河原溫的創作始終圍繞 「時間」與「存在」展開。「日期繪畫」《今日》系列近三千幅作品,構成了一部跨越 48 年的視覺日記。每張畫布不僅記錄了具體日期,更通過裝載畫作紙箱中的當地報紙剪報,將個人生命軌跡與歷史事件並置。例如 1969 年阿波羅 11 號登月期間創作的三幅大尺幅畫作,既是個人記憶的見證,也是人類歷史的切片。這種將日常記錄昇華為存在冥想的能力,使河原溫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編年體,成為對生命本質的深刻叩問。
這些作品的「河式特殊性」,首先體現在他個人性格的神秘之處。河原溫終生拒絕出鏡,他從不參與自己展覽的開幕式,也從不接受採訪,只通過作品與世界溝通,給觀者留下了神秘伏筆。他的資訊卻通過明信片背面的起床時間、地圖上的紅色軌跡、遇見者的姓名列表,構建起比自拍照更私密的精神肖像。



| 紀律性傳承:當代的「打卡」藝術
河原溫對「時間媒介」的創造性使用,直接催生了當代藝術中的「延時性實踐」。謝德慶 1980-1981 年的《打卡》系列,正是對河原溫紀律精神的激進回應:藝術家在紐約東村租用工作室,每小時準時在考勤卡上打孔,持續一年,最終留下 15000 餘個打卡痕跡。與河原溫的「日期繪畫」一樣,《打卡》拒絕美學修飾,以機械重複的動作將生命簡化為時間刻度,二者共同構建了「通過規則凝視存在」的藝術譜系。不同的是,謝德慶的打卡充滿生存焦慮(考勤卡象徵資本主義勞動異化),而河原溫的日期書寫更趨近於存在主義的自我確認 —— 前者是對系統的抵抗,後者是對系統的馴服。
河原溫的《我起床》《我遇見》等系列,也預示了當代藝術中數據視覺化的潮流。蘇菲·卡爾 1979 年的《威尼斯套房》跟蹤陌生人的旅行,以攝影與文字記錄構建私密敘事,其對日常細節的偏執捕捉,與河原溫《我遇見》名單(每日打字記錄遇見者姓名)形成跨時空對話。更具反差的是楊振中 2000-2003 年的《我會死的》系列,邀請全球參與者直面死亡,作為河原溫《我還活著》的反面鏡像,二者共同構成對生命兩端的凝視 —— 前者是積極的存在宣言,後者是消極的存在省思,卻共用著將個人經驗昇華為集體命題的藝術野心。
或許在於他早已洞悉到今天社交媒體的核心功能:位置通報、狀態更新與日常生活分享。他的郵件藝術計畫也與之相呼應。河原溫的藝術之所以在離世十年之後仍引發震顫,在於他提前半個世紀預演了人類在技術時代的存在困境。


| 展覽空間敘事的四重奏
大館的獨特之處,首先在於其對展覽生態的精心編織。藝術家書籍圖書館兩期專案 「只有此處,重回此地」 如一對鏡像,以印刷品媒介為經線,將國際當代藝術家的私密敘事與河原溫的宏大體系編織成網。第一期裡,書信、地圖、明信片等日常物件掙脫實用功能,成為捕捉人際連結的 「存在容器」;第二期則以河原溫的系統性創作為錨點,讓那些曾在數碼浪潮中被稀釋的 「記錄儀式」 重新獲得重量。這種策展策略暗合大館作為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的歷史肌理 —— 當殖民時期的建築空間容納著最先鋒的概念藝術,物質載體與精神內核形成奇妙的時空對位。
河原溫展覽的呈現方式更見大館巧思。四塊展區如四部樂章。展覽第一單元「開放的系統」集中呈現河原溫的郵件藝術與時間巨構,其中《我還活著》(1970-2000)系列電報堪稱存在主義的極簡宣言:藝術家以十年一次的頻率向特定人士發送電報(Telegram),內容僅為「I am still alive」疊加自己的名字。
從早期「我不會自殺」的焦慮陳述,到最後定格的「我還活著」,九百餘份電報因各地郵電系統格式差異呈現的偶然視覺性——機器郵戳的標準化與手寫地址的隨機性並存,恰似個體在龐大社會系統中的掙扎與確認;這種將藝術控制權讓渡於外部系統的姿態,與《我起床》(1968-1979)明信片系列中,他每天向親朋好友、收藏家和同事寄送兩張明信片相似。每張明信片上,他都蓋上日期、自己的名字、現住址、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英文大寫的「I GOT UP AT」和他起床的時間;《我遇見》以打字機逐日記錄相遇者的姓名列表;《我去過》在地圖上標記行進軌跡;《我閱讀》則保存當日報紙,常與對應日期的《今日》畫作並置。這些明信片的材質形成關聯:批量生產的觀光圖像背面,工整蓋印著每日起床的時間,觀光景觀的公共性與私人作息的私密性劇烈碰撞,同樣預言了現代時代社交媒體的「親密焦慮」悖論。


耗時28年完成的《百萬年》系列,是一個由24件作品組成的不朽系列,他將時間尺度推向宇宙維度。其中包括獻給「所有活著和死去的人」的《百萬年:過去》卷從西元前998031年逐年紀錄至1969年,花了兩年時間完成;獻給「最後一個人」《百萬年:未來》卷從西元1981年延伸至1001980年,創作歷時18年,每本活頁夾頁面以五百年為網格單位,兩卷作品在1970年-1980年刻意留白——這十年空白既是藝術家創作生涯的「此時此地」,這些體積加起來有200萬年的歷史,更是對人類時間局限性的詩意隱喻。

第二單元「今天」以近三千幅「日期繪畫」構建起嚴整序列的視覺編年體,以「六個年代」「七天」「環太平洋」「1987 年 5 月 1 日」四個主題解構其創作邏輯。1966年1月4日,他創作了第一幅「日期繪畫」——在單色畫布上只使用白色繪製日期——這幅作品共同構成了他畢生創作的《今日》系列,看似簡單,實則耗時費力。需要先塗4層底色,通過精心調和達到微妙的色彩層次,待乾透之後,再極其工整地書寫日期,平均耗時約8小時,如同日常工作。這些作品有8種尺寸,從8x10英吋到61x89英吋。除了在畫上所標注的日期,一些也記錄著個人趣事,例如「今天我和約瑟夫(Joseph)、克莉絲汀(Christine)和弘子(Hiroko)玩大富翁,我們吃了很多義大利麵」(1968年1月1日),並且按照一系列不變的步驟精心製作。如果一幅畫在午夜之前沒有完成,他就會銷毀。河原溫為每一幅「日期繪畫」製作了一個紙板儲物盒。許多盒子裡都襯著當地報紙的剪報,將日期的標誌與當天事件的喧囂並置。
其中,「環太平洋」系列尤為值得玩味:藝術家在東京、紐約等太平洋地區不同地點創作的畫作,紙盒內襯的當地報紙成為隱形的「地緣日記」——1968 年墨西哥城學生運動的剪報、1995 年阪神大地震的報導,與單色日期形成蒙太奇般的敘事張力,同時也揭示時間記錄的多維度意義。在 48 年間,河原溫在全球 130 多個地方創作了數千幅這樣的畫作。

第三單元「日常現實的編年史學家」聚焦 1978 年河原溫在香港的五日停留,成為展覽的情感錨點。46 歲生日當天創作的《日期繪畫》,畫布上的日期筆觸因酒店臺燈的暖光而微顯顫抖,有意思的是,日期書寫格式根據所在地語言習慣進行變化:英語區(英式/美式)對應格式(DD/MM/YYYY或MM/DD/YYYY);非拉丁語系區(如日本),使用世界語(Esperanto)書寫日期,這種變化也記錄了藝術家當時的所在地。《我遇見》活頁夾中模糊的人名與《我去過》地圖上的紅色軌跡交織,勾勒出一個城市在殖民末期的日常肌理,揭示出「全球公民」敘事下的在地性話語。
第四單元「純粹意識」中敘述七幅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7 日的「日期繪畫」,今年較早前在香港上水禮賢會幼稚園展出,與包括跨境學童的多元背景園生共處兩周。沒有講解、沒有標籤,孩子們在畫作旁玩耍、午睡,意圖反映基本性的學習概念,自然生成的互動影像被記錄成書 —— 這是對河原溫「藝術應超越闡釋」理念的實踐,他讓四至六歲兒童以直覺感知連續七日的灰色變化,讓孩子們自然地與之相遇,自1998年起,裝置已到訪了二十九個教室,並仍繼續它的環球旅程,每個所到之處皆以書冊出版記錄展覽詳情及孩子日常活動的相片;恰如河原溫以一生 29771 天的數字傳記,將生命簡化為最本真的時間單位。
展覽拒絕了傳統美術館的白立方霸權,轉而以檔案式陳列、現場朗讀表演、文獻並置等手法,讓觀眾在物質細節中觸摸到藝術家用生命書寫的存在詩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館藝術家書籍圖書館與百萬年基金會的合作,將展覽延伸至出版物與公共專案,使河原溫的「時間哲學」從展廳走向更廣闊的文化場域。
| 印刷媒介的當代性重釋
河原溫的創作充滿了對「控制與失控」的辯證處理。《我還活著》電報依賴當地郵電系統的格式規範,地址標籤的手寫痕跡與機器郵戳構成偶然與必然的對話;「日期繪畫」的嚴格創作流程雖限制了自由,卻通過手工筆觸的細微變化,讓每幅作品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證據。這種在規則中尋找自由的創作哲學,在規律中探尋時間、存在的本質,剝離敘事與情感渲染,直指生命本真,同時也暗合了大館展覽標題「自由之律,律之自由」,揭示規則與自由的共生關係——規則非束縛,而是通往自由的路徑。
大館對河原溫作品的物質性呈現,也尊重藝術家原來的創作方法,用最質樸的方式(明信片、電報、畫布)讓觀念落地生根。那些邊緣泛黃的明信片、帶有折痕的活頁夾、顏料滲透的畫布肌理,構成了對「非物質性」的溫柔反叛 —— 原來最深刻的哲學思考,從來都需要物質載體的托舉。這樣的概念,恰好也與大館作為實體空間的文化使命不謀而合:在這個數字複製氾濫的時代,唯有真實的觀看、觸摸、體驗,才能讓藝術成為抵禦存在之輕的堡壘。
結語
展覽特別設置香港專題展區,聚焦河原溫 1978 年 46 歲生日期間的停留,深化了「世界公民」身份,揭示個人記錄如何承載地方歷史。在大館前域多利監獄的殖民建築空間中尤為凸顯 —— 當先鋒概念藝術與歷史建築相遇,物質載體與精神內核形成奇妙的時空對位。在這個「自我」不斷被確立又被否定的時代,河原溫的作品提醒我們:真正的存在,不在像素的閃爍中,而在紙頁的褶皺裡,在時間的裂縫中,在每個用心記錄的「此處」與「此地」。
文|ASY
圖|大館當代美術館
「河原溫:自由之律,律之自由」
策展人|侯瀚如與郭瑛,秦文娟協力策展
日期|2025年5月23日至8月17日
週二至週日早上十一時至晚上七時
週一閉館(公眾假期照常開放,延至翌日閉館)
地址|賽馬會藝方一樓展廳及F倉
——— 探索更多藝術地圖 ———
資訊投稿 |editorial@artmap.com.hk
@artmap_artplus
@artplus_plus
@ampost_art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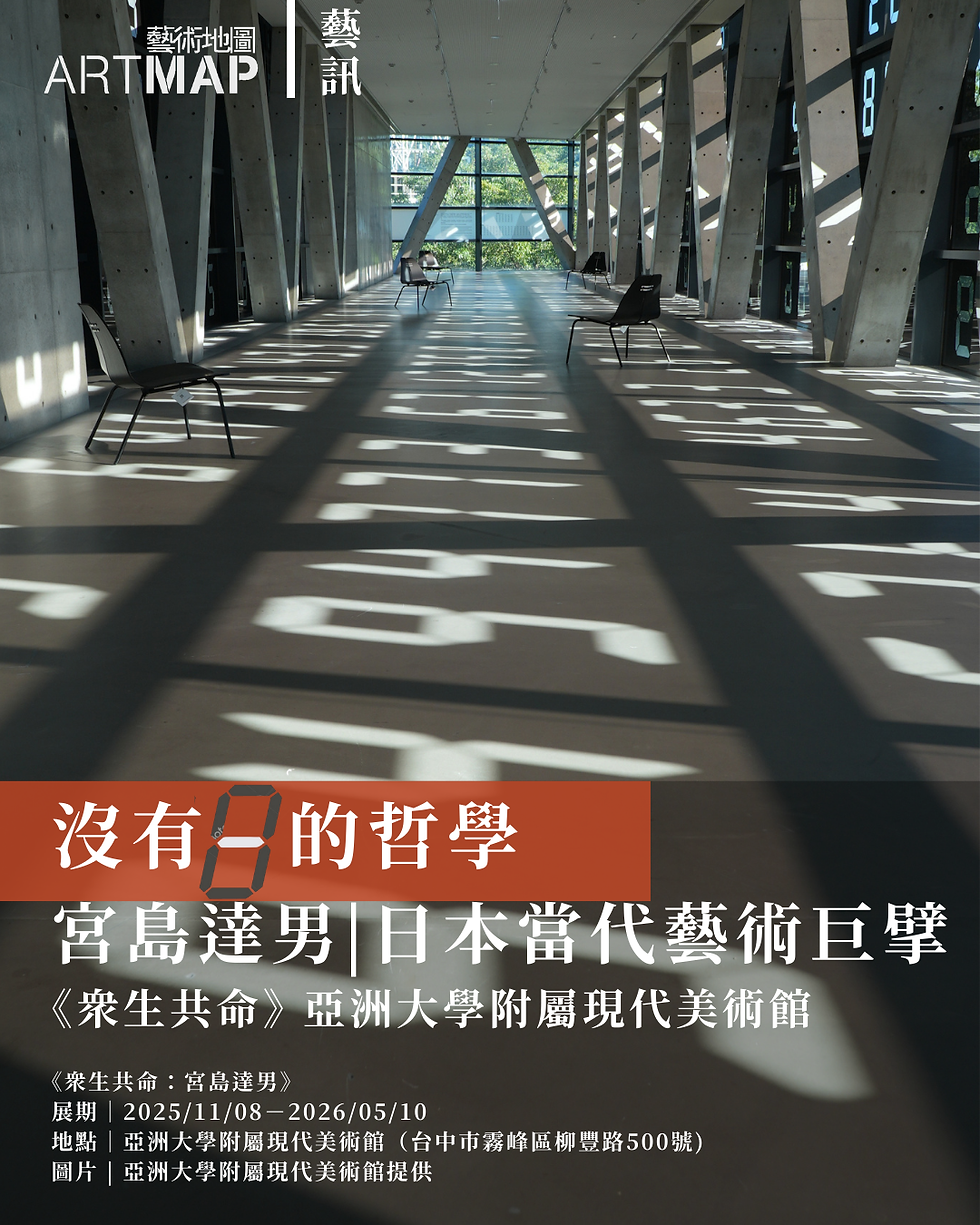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