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評論家 | 共和的祭典 | 綠葉劇團《山海經》第一部曲《山川命・終章》
- experience am space

- 2025年10月3日
- 讀畢需時 7 分鐘

到最後,幕沒有落下來。循着非洲鼓與和聲,一趟意想不到的淨化啟程了。綠葉劇團《山海經》導演黃俊達於劇終致辭:祝福觀眾有「山神的保佑」。

借着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的地利,隊列如重生般踏出劇場,穿過儀式感的火爐,沿林間小徑步去遠眺維港的高台前。剎那間,我們從遠古奇書的畫面穿梭到身處的真實。觀演時是晚上,演員此刻容許靜默的留白時間,戲劇堆疊的異化情感,更一次倒溢在如真似幻的萬家燈火。
我想觀眾跟我一樣,分不清是彩蛋,還是劇本要求,演員圍着火爐邀舞狂歡,團聚的熱烈打破了本有的深沉,還之以舞步的輕盈,甚至將主角丹朱化作的鴸鳥道具巡遊眾前,反常地將幕後搬到了台前。這一切,宛如祭神後的部落儀式,又再回到生活。事實上,由於整齣戲劇強調異化,離劇場空間而去的集體參與,有助觀眾「回魂」,重新連結現在。
綠葉劇團(Théâtre de la Feuille)於2010年在巴黎成立,巡遊多年,近期落腳香港,是近年備受關注,研究形體劇場的劇團。他們於2024年底展開了為期半年「叩問傳統.思考當代」身體訓練研究計劃,演員都是學員甚至導師。《山川命・終章》濃縮了「叩問傳統.思考當代」計劃中,戲劇及技藝的參學成果;激盪在人與獸的英雄敘事,東方概念及形體美學,化用於先秦經典《山海經》背景,最後昇華為《山川命・終章》的祭典現場。

《山海經》去日已遠,劇場詮釋先秦人民消災祈福「儺」的祭祀文化,於宗教、文明、生態的交界,探尋自然神話與現代文明的呼應,不難相信也有解魅神話形象和信仰文明的含義。它帶我們體會宗教神話的真善美,諸如有專注、奉獻和堅定的形象,貫穿整齣劇,也告訴觀眾,善惡不只兩面。
故事是人面對自然與超自然的不自量力與永恆探索:王子丹朱下棋時聽見異國士兵的分享,發現外面世界的奇妙,決定登上靈山,卻發現山神已去,欲招其魂而尋助於巫,誰知落入圈套,復活了各種怪物。
|陌生而新鮮,有增值、再造與超越經典的野心
可以相信,這齣戲劇不走回頭路,刻意讓我們感到陌生而新鮮,以一種安全的距離,上演稟神問道,散發着類似「幽玄」和「崇高」的審美。我感受到增值、再造與超越經典的野心。

昏暗的極簡圓形舞台上,懸着似蛹繭的大型掛布,惹人猜測生死的意象。劇裏曾出現「吊鋼絲」人手特技,韓梅主演的王子丹朱還真的吊升並臥藏其中,以身祭山。不追求最新科技潮流,帶點人工味道的技術可以是黃俊達導演說的「呃(欺騙)tech」[1]延續。帝堯的長子丹朱由女性演出,與歷史想像不同。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堯說他「頑凶,不用」。堯禪讓於舜,丹朱遂被流放,謀反失敗而化鴸鳥。劇場故事設計則聚焦於丹朱上山之旅的大我精神和他與獸的互動。
演員選擇於中後段謝幕。一鞠觀眾,二躬面對觀眾的牆,也整齊跪坐,凝視牆,似等待着甚麼,也似是神靈降臨了——那面似是有形卻無形的牆,我們見到了甚麼?
除了舞台,服裝不復刻華麗古裝,反而呈現一致暗沉的黑色:絨毛腫脹的窮奇、倒轉穿羽絨的蒙面六巫、戴能劇面具的村莊父女、無臉茅草面具的刑天⋯⋯唯獨臂神鳥穿得像木乃伊,亦都奇裝異服,這取向恰好對應了《山海經》稀奇怪誕的人物造型,設計出暗黑幽深的巫覡場景。

大家可能知道,夸父逐日也是《山海經》的故事。夸父逐日而死,丹朱救山而亡……
|超越文化、地理與文本限制的人話與非人話
開始時,演員分三角而坐,產生結界氣場。高頻的唱白念誦(chanting)統整了丹朱入山之旅,混合樂隊的空靈搖滾音樂,營造了神聖而遙遠的時空。台詞捉摸了先秦文風,常用四言斷句,輔以重複與對偶,或和唱,或疊唱,更聽見「兮」,讓人想起《詩經》與《楚辭》句章,卻不拘泥其中節韻。唱腔呢,有時尾音或拉高拉長,像唱聖詩,想必參考了戲曲唱腔。
戲劇標榜運用了粵語、普通話、中國方言、英語、意大利語、馬拉雅蘭語及梵語——多語集合,實不常見。雖知道表演的國際班底來自中國內地、意大利、印度、日本和非洲等地,導演沒有統一語言,讓演員詮釋母語,保留其根性。黃導演曾於報道說:「人的善惡、上山的慾望,以至怪獸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跨文化、跨地理的東西,需要有這種選材。」我想,無論國際議題、民族共融、物種共存或天地起源,缺少一塊拼圖,都不算完整。這種複雜文化背景的陣容, 剛好可拼合出超越文本限制、追求普遍性的拓撲空間。一般而言,本地觀眾只聽懂粵語,異國語言對白於是被消解,嬗變非語言理性的感性體驗,與之互相映照,若單語演出是無法呈現的。場上,異國語言分別出現,有時,代表山鳥啁啾,有時,則是奇獸鳴叫。聲音之不可理解,不就是當我們聽鳥鳴獸啼時自然產生的區別嗎?
同時,這也是略過而聽不見的聲音。出現的妖怪,沒有高聲吟唱的戲分,只有邊緣化、偶爾露面的感述和舞動,彷彿暗示人獸有別,獸聲終究不是人話。導演以語言隔閡和反襯強調了「人話」的主流視角與「非人話」的孤立局面。我想,無論甚麼場域裏,那也很常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怪獸也有「人味」,反之亦然。獨臂神鳥念充飢之恩,為救丹朱犧牲己命。丹朱受助於獨臂神鳥,才可尋得啟示。於在古典中,窮奇、窫窳也曾被記載是善良的天神。丹朱終也化鳥,殊途同歸,應當他是人是獸?是人是獸,準則在哪?恐懼與信仰息息相關,也構成了善惡觀。文本創作的米哈提醒我們,「口耳相傳的鬼邪」是「文明告訴我們的事」。劇中人獸互動:滅與被滅,進擊與躲避,不外乎傷害對方。人的一方是被動也是主動的惡,似在提醒,我們都一樣。
劇場更請來了樂隊演奏,這樣便成為了齊數的戲班。合作的香港獨立樂隊The Hertz,主要是男中低音吟唱,配以電子樂器,偶爾混入女和聲與龐克失真音,或激昂或沉澱。合成器的底律,締造了奇幻、迷離與遼闊的音樂山林。與劇本一樣,他們不執着於重建歷史的古雅,據說參照了不同地方的祭祀音樂,營造了幽林中神祕、憂心與崩壞的緊張氣氛,讓人想起屈原回望故國的心境——要知道屈原作品大量取材於民間祭曲,糅合了楚人文化的神靈傳說。王子丹朱驚喜地演繹了屈原《九歌》本應憂怨的《山鬼》,成為其山中遊記插曲。樂隊演奏創作曲目《山問》放在劇尾,就像楚辭體常見的亂曰,道出「你在明或暗」敲問,有行動呼籲的感覺。
|取材亞洲傳統神靈舞劇和祭典儀式的動作,思考藝術共和的現在與未來
劇中特別的動作很多,放在《山海經》的世界裏,彷彿是為了不能被理解的「他者」表演。演出隊伍請來了跨界別、跨文化的亞洲導師,消弭「他者」與「我們」的距離。觀眾不一定會理解全部涵義,每人解讀也不一樣,這正正是這遠古奇書之於今人的情況,也為經典及戲劇帶來了普遍意義。開頭有一段是類似千手觀音的圖騰動作,你猜是甚麼作用?眾人包圍丹朱,套上紮作的圏,你猜又是甚麼意思?有些動作,當下便達成意義。有些,則下回分曉。跪坐、膝行是日本榻榻米室內莊重禮儀,在戲劇中卻被大膽採用。試過跪坐及膝行的人便知道,儀式都是為了尊重、莊嚴,符合禮數會得到距離的平靜。
於復活死山的最後一著,六巫喚出了唯火可傷的窫窳。日本劍道家後藤佑介演的無頭怪刑天再度出場,上演動作獨白。這次不向主角揮砍,而向無形的敵人開戰。劍一出鞘,就被點燃火油。他心如止水,氣劍體合一。隨着劍揮舞加速,火越燒越旺,驚心動魄之際,他一合劍魂。劍舞令人感到危險中的篤定,也聯想起被吃肝的普羅米修斯,那種永恆的苦,被凝練為美的創造——一日為匠,一生為匠,便超越了匠的「職人」。

同是劇場創作者及演員的Remith Ramesh飾演窮奇,引入印度喀拉拉邦庫提雅坦梵劇特色。聽綠葉劇團對Remith Ramesh的訪問提及,他也借用了另一印度古典舞劇卡塔卡利活力的形式放入表演中。原來,庫提雅坦梵劇節奏緩慢細緻,未必能在2小時的劇場中悉數展現魅力。如果你離舞台夠近,會看到他瞪大眼睛傳神,擺出四肢平衡像「卍」的姿勢。救助村民,也為人所害的形象,令人思考在印度文化中,會不會也有善惡顛倒的對應?
這兩個外借文化的悲劇角色,加上不同文化舞台動作的借鑑,融入經典再造的唱白敘事,帶出亞洲傳統神靈舞劇和祭典儀式作為藝術戴體的兼容、靈活與實驗可能,折射出解構後的戲曲和形體劇場新的走向。背後藝術共和的價值,值得用以思考亞洲藝術或藝術本體的現在與未來。
《山川命・終章》打響了頭炮,還只是序章。綠葉劇團計劃塑造《山海經》三部曲。依他們說,「以《山海經》為創作的根,不只是因其描述天地之始,更是透過宇宙與人類的起源發問,重新思索生命存有的意義與價值,並以超自然現象和幻想去探究原始」。憑着《山川命・終章》高度凝煉的文化張力,併發出劇場藝術兼容力,以及受訓國際班底呈獻的史詩級演出,那種篤定、熱誠和嫻熟,讓劇終時很多觀眾仍在夢中,無以名狀。
文|黃君凱
圖|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觀賞日期 | 2025年9月13日7:30 pm
觀賞地點 | 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
——— 探索更多藝術地圖 ———
資訊投稿 |editorial@artmap.com.hk
@artmap_artplus
@artplus_plus
@ampost_art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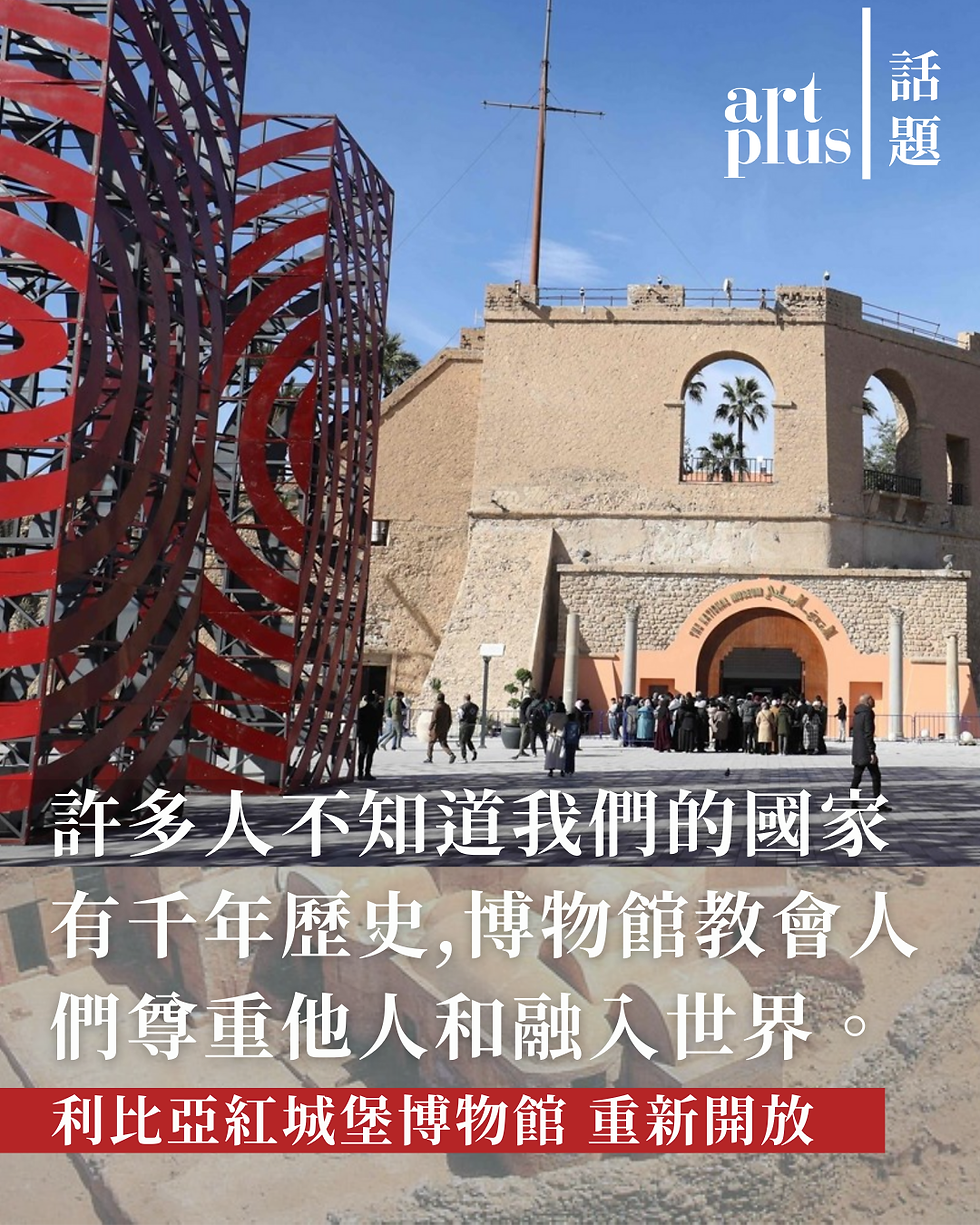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