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評論家 | 專訪藝術家蔡國傑 | 誤差為刃:以藝術解構制度
- experience am space

- 5月8日
- 讀畢需時 26 分鐘

「我就生活在『無間道』中」,蔡國傑這般自述。此「無間道」援引自《涅盤經》,原指無間地獄的永恆之態;於他而言,這成為其藝術實踐的發軔之端與創作張力的驅動之源。在地界與群體的空間隙縫之間,他持續叩問土地權力,於
當代社會的紛擾土壤中蔚起藝術項目,診察諸般社會議題表像下潛藏的隱微脈絡。
一、 土地權力:蔡國傑的空間政治
蔡國傑錨定土地測量誤差這一切入點,對現代社會土地所有權的既定概念發起質疑。基於日常對土地規劃、買賣流程的細緻觀察,他意識到測量制度下土地界線的普遍誤差,挑明地籍圖在現實情境中的「精確」假象,將其上的邊界線條視作誤差空間,進而衝擊傳統的土地權屬觀念。自 2004 年臺北「開店買賣」的初步嘗試起,他有條不紊地拓展自己的藝術表達,緊扣「誤差」核心,探究土地權屬背後的隱而未現,開啟持續發力、劍指土地權力深層架構的藝術探索。
1.1 土地所屬與誤差空間
現代社會為管理居住空間的而對空間進行編碼的地籍測量,在蔡國傑看來還關涉到對空間正義的探求。被編入地籍的空間測量過程中似乎獲得了合法地位,而未被認可的「野生」、「自由」、「誤差」空間的被邊緣化。這種編碼過程的「誤差」是蔡國傑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概念。他思考到,當一塊地將被人群使用前,無論是共有還是私有形式的土地分配,通常會有某一方對其進行規劃。然而這些土地在測量和劃分後的每條界線本身就因技術原因而不夠精確,必然會產生測量圖與真實空間之間的誤差。由此,蔡國傑認為地籍圖上的所有線條在現實中都是誤差空間,地籍圖即可被視為「誤差圖」。
由此,蔡國傑孜孜不倦地拓展開了他的「誤差事業」。從 2004 年開始,他在臺北進行了「開店買賣」的嘗試,將對「誤差」的初步思考轉化為藝術行動,並逐漸發展出更多關於「誤差」的藝術表達。在「停車格租賃地攤商售」(2004)中,蔡國傑通過支付停車費租下停車格空間,擺地攤售賣物品,這些行為微妙地挑戰了土地使用權的傳統觀念。在「線性商店:介面實體店」(2005)中,他不但在店面的側面外牆貼上商品貼紙,開設實體店,還在店鋪內設置互動裝置,邀請觀眾參與其中,像模像樣地展開了「實體店鋪」的商業行為。
在長達十餘年間續進行的「誤差簽售」行動項目中(2005-2019),蔡國傑在多個城市的市井街道進行調研,確認自己對誤差的敏銳察覺,並在地籍圖上標注出各段地籍之間的誤差空間。以《安居地》(2019)展覽為例,他以東方基金會舊址為中心,印製了附近兩三百米範圍的地籍圖,通過貼膠帶等方式標記建築與人行道之間的邊界空間,並在地籍圖上標紅,向民眾解釋所售為各段地籍間的誤差空間。蔡國傑強調:「我賣的是政府放棄的」——他嚴謹考究各地土地律法條文,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挖掘那些被忽略的細微誤差,將它們提標出來;為了使簽售行動更加正式,他從民間通用的土地合同出發,逐步製作了符合誤差簽售的清晰條文,確保選品、確認、支付、簽字蓋章等買賣流程嚴格按照商業條例執行。臺北、台中、板橋、澳門,甚至佛羅倫斯、柏林,每次他在「誤差簽售」展場向觀眾解釋所售為各段地籍之間的「誤差空間」,引導觀眾好奇買賣者與商品之間權屬關係的依據所在,借由藝術視角揭示制度運行所牽涉到的土地測量誤差、土地所有權的模糊性。蔡國傑意圖以藝術的方式掀起土地與權力之間微妙關係的掩飾,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既有制度的合理性。

至 2020 年,在展覽《選擇分之所有》的「誤差計值」專案中,他基於臺灣的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3 條條文中所明確的「標準誤差尺寸」(2 公分)與「最大誤差尺寸」(6 公分),計算出環繞「伊通街地號 89 號土地」的「邊界」這一誤差間隙面積。在熟識該地詳細的物理、經濟和社會資料後,他與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協同完成對這片土地邊界進行具法律效力的估價並得到《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進而將所得到的「標準誤差市值「和「最大誤差市值」的區間數值打造在兩塊金色牌匾上,連同在這一社會調研過程中的法規文獻材料一併公示於展場。

蔡國傑將土地所有權問題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下進行探討。蘇賈(Edward W. Soja)指出,在超越傳統二元對立的空間概念之外,還有融合了多重視角、經驗和文化的「第三空間」。蔡國傑在其「半田計畫」藝術專案中創造第三空間,通過觸碰大眾關注點,介入制度誤差的空間專案探討,並提醒公眾— —土地的意義不單是物理實體,更是權力鬥爭和社會關係的象徵;土地是不同權力鬥爭的場域,鬥爭也在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1.2 土地開發與社會正義
通過批判性審視土地開發專案,蔡國傑將反思的矛頭指向了地產開發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質疑其中隱含的權力結構和對居民權益的影響。正如大衛·哈威(David Harvey)認為儘管資本的積累和流動是城市空間變化的主要驅動力,但社會不平等和資源的不均衡分配也伴隨而來。蔡國傑在藝術專案中將各地地產開發對社區的影響、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等掩藏在土地開發進程中的問題暴露於公眾視野,呼籲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蔡國傑常常有意識地將很多社會場景導入展場,架構新的對話模式。在「半田土地開發暨地產博覽會」專案中(2019),蔡國傑將展廳空間重新搭建,邀請澳門多家地產公司分派銷售專員來到現場台位做專案商售。地產員工們在其展位中陳列租賃資歷證書,對觀眾(在此時也同為地產顧客們)宣講各自的待售項目展覽《安居地》「半田土地開發暨地產博覽會「專案(澳門·東方基金會,2019)單元。藝術觀念與公眾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在展場中的互動中拉進。藝術家構建並觀察這一場景,實現了對空間和事件的權力反轉——是地產商進駐這裡、向藝術家承租展位,參與進藝術家對土地開發展開討論的這場展覽、成為了藝術項目的一部分。


《交易繼續》展覽(紐約,2020)則是對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地產商身份背景及其基於自身利益而貫行的政策提出批評。展覽通過三個專案多面向地諷刺川普在疫情期間的政策施行,揭露土地資源開發和流轉過程中的利益衝突和權力濫用。在「第一樁交易:牙買加莊園」項目中,蔡國傑關注了在這裡度過少年時光的川普對有色人種的歧視,通過讓觀眾接受「白化」和讓有色人種認領川普出身地的地籍線,蔡國傑啟釋土地開發背後的種族問題,敦勸關注地產開發和居住社群中的種族問題、社會不平的不斷加劇等。在「交易繼續:英雄進不了的酒店」項目中,他批評川普在疫情期間利用聯邦法律要求其他品牌酒店向群眾開放、卻保護自己旗下酒店的偏袒政策。通過佈景出川普酒店中幾乎相同的場景,蔡國傑質疑這位政客在公共衛生危機中的角色和擔當、資本積累者對社會需求的有意忽視。通過在「最後的交易:白宮大廈」項目中以對川普大廈(其競選總部)地籍線之名來進行實為白宮地籍圖的出售,蔡國傑諷刺了政治與資本的沆瀣一氣,兜底資本對城市空間和居民生活狀態的塑造之力。以如此針對川普地產政策的批判,《交易繼續》展覽嘲弄了地產資本對公眾生活的影響;在此,藝術充當質疑社會不公的有力工具作用盡顯,銳利如刃。

1.3 土地邊界與身份政治
蔡國傑關注並探討土地邊界與身份政治之間的交織關係。通過「柏林的長度」、「航行中」和「家園」等藝術專案,他持續標示、強調物理空間的實在邊界,更提請深入思考這些邊界對塑造個體和群體身份的塑造、它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意義。
「柏林的長度「(2019)借紀念柏林牆倒塌 30 周年反思城市過往中的地界劃分制度。蔡國傑將全長 167.8 公里的柏林圍牆(曾經權力分屬的國別分界),以每一公里為一單位進行地籍編號,並通過在互聯網進行拍賣,在超越以往的覆蓋範圍上邀請人們重現相關的共同記憶,探討實體邊界的構建對彼此身份認同和集體記憶的影響。他還以柏林牆所在的地址申請了國際銀行 N26 的銀行帳戶,將「誤差售賣」系列專案所募錢款悉數存入「柏林圍牆」之名的帳號中。這份存款在金額數位之外,更承載了作為人群身份經歷政治塑造的邊界表徵。
2008 年柏威夏寺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卻引起了泰國與柬埔寨之間新一輪的主權爭奪;蔡國傑關注到了這場紛爭,以此為契機展開了「航行中」專案(2021)的籌備。他遵循當地航行器司法權延伸的概念(航行器臨時登記證),讓無人機從曼谷經空、陸路航行至泰國與柬埔寨相接、長年備受爭議的國界地帶,做技術性墜毀後拍攝這個地界仰視的天空,以藝術之名宣告邊界上的間性空間。該專案以「落地」、「攝天」的方式見證了在權與利的爭奪激化下,原本萬物生活區域朦朧的過渡地帶向被嚴密計算、嚴格管控的政治邊界的演化。傳統的自然地理空間逐漸被社會構建的空間所取代;無人機的「殉葬」嘲諷了這場有違人類對和平追求的無益紛爭。


《曼谷雙年展》「航行中「專案(曼谷,2021)
「家園」(巴黎,2019;李雅斯特,2020)項目則使這一議題進一步深化,直接觸及了國家之間的戰爭、對國境地界約定的破壞紛爭,引發人們對腳下所踩土地、身處之空間的反思。他邀請難民繪製他們記憶中的家園,並出售這些記憶的邊界。在與難民溝通、重建他們與土地聯繫的過程中,蔡國傑與難民一同探討身份、記憶與所有權等議題。因國別矛盾,難民們在政治鬥爭中顛沛流離,個體與群體的身份認同感遭受強烈衝擊;蔡國傑的努力讓這些衝擊背後的聲音與故事得以被傾聽,引發國際共情。
蔡國傑如反芻一般咀嚼土地邊界與身份政治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他探討這些邊界對個體與群體生存境遇的塑造,又怎樣影響他們在身份認同過程中的協商與抉擇。與此同時,蔡國傑聚焦於在全球化浪潮與現代社會背景中成為政治權力鬥爭焦點的土地邊界,思考其確立與瓦解的動態過程給游寓人群所帶來的命運起伏。
二、人文關懷:蔡國傑的群體關注
自進入對「土地」議題的藝術探討以來,蔡國傑覺察到人們在追求「安身」的過程中,內心的荒蕪使他們離「安身」越來越遠。他從對土地邊界的關注更明晰地拓展到對土地上「人」的深刻關懷,觸及邊緣人群的生活狀態和心理體驗。通過藝術實踐,蔡國傑為他們提供社會參與和自我表達的平臺,分享他對人類群體細膩而深厚的關懷。

2.1 家園與個人記憶
蔡國傑在田野中體認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人群在物質支援和制度倫理保障展覽《阿波羅計畫 第三回》「家園」專案(巴黎·AMAC Projects 當代藝術中心,2019)方面的困境。「家園」專案先後在法國巴黎和義大利的李雅斯特展開。在巴黎,藝術家邀請流離失所者繪製他們記憶中的故鄉;再伴隨地界所有權轉讓的契約簽署儀式,以象徵性的價格出售給藝術家。在李雅斯特,蔡國傑線上完成了與 19名遷徙者的家園輪廓的轉讓協議。這些經藝術行為對特定身份的確認,是對邊緣群體的記憶經歷的理解、接納、尊重和認同,為他們提供了表達和重構個人歷史的空間,引發全球性難民現象的對話。
「家園」專案的展開中,蔡國傑改觀了對「難民」們的既有印象。這一群體並不認同「難民」標籤,而稱自己為「有特定身份的遷徙者」。在巴黎街頭,蔡國傑採訪他們因何至此的經歷故事,請他們畫出陷入戰火前的家園地圖,框示出住宅的地籍邊界,將這段記憶「售賣」給他。通過這樣的藝術舉措,漂泊他鄉的遷徙者從「失去者」、「講述者」變成了「擁有者」和「出售者」;他們所繪製的輪廓在代表居住空間的實體劃分意義上,也標記了自己的身份和生命歷程。蔡國傑與他們探討:「賣掉」是否意味著放棄擁有?賣掉記憶中的故土是否擺脫了內心的艱辛、感到輕鬆解脫?在與遷徙者們互動而碰撞出而越發多元的瞭解下,群體性的「難民」標籤,此刻顯得蒼白無力——它過於籠統、含糊,無法真切觸及每一個個體內心深處複雜而獨特的情感世界,因而難有實質意義。
有的參與者僅畫下一個人形來表示「家」,認為「我存在的地方就是家」;還有些人在售出「家園」後又羞澀地返回,希望撤銷這份合同,坦誠自己不願告別那份情感眷戀。對許多人來說,繪製家園的過程既喚起了美好的回憶,也帶動痛苦化作淚水宣洩,流露出「家」這一概念在情感層面的複雜性和多重意義。通過邀請遷徙者繪製他們記憶中的家園並出售這些記憶的邊界,蔡國傑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表達和重構個人歷史的契機,還借助數位化網路平臺的線上售賣和傳播效應,讓更多人瞭解到這些遷徙者的背景和經歷,增進了城市機構對遷徙者需求的理解和支援,也進而宣導根據群體差異制定具有倫理內涵的關懷路徑,保障個體的自我價值感,使他們有尊嚴地悅納關懷。

「家園」項目於 2021 年摘得「高雄獎」首獎。常言「故鄉是你的後路」,但在俄烏戰爭、阿以衝突等硝煙下,流離失所者的「家園」土地可念而不可及。令人欣慰的是,複雜的社會互動和演進的話語實踐不斷重塑「身份」的概念;蔡國傑所發起的「家園」項目也由此突破了最初聚焦難民群體的狹隘範疇,延伸至更為廣泛的、處於心靈層面「遷徙」狀態的人群,探討人類共通的、隱秘而堅韌的情感紐帶與深層歸屬需求。蔡國傑以「家園」項目發問:當物理存在變動不居,究竟何處才能護佑心靈、寄託情感?在現代社會的快節奏中,人們碌碌追逐物質豐盛,該如何確保心靈深處柔軟而真切的需求不再被無情地忽視、長久地懸置?
2.2 城市與住民意願
在當代社會,城市已成為人類生活的核心場域,凝聚了民眾對「家園」具象且真切的感知,承載對美好生活空間的種種期許。城市圖像作為人們凝視城市、賦予城市獨特意義的視覺媒介,既涵蓋城市測量所得的地籍圖,也包括蔡國傑別打造的誤差藝術空間。這些圖像不單記錄著物質空間的表像,也在具象化地呈現社會關係脈絡、權力結構佈局和多元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城市內在肌理。
蔡國傑憑藉敏銳的洞察力捕捉到城市發展進程中的諸多潛在問題。在資本大量湧入城市建設領域之際,城市居民追求理想居住空間的過程屢受阻撓,常陷入資本佈局的「陷阱」。
「有沒有想過,可能我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就要這樣不划算地投身在這場看似獲得巨大成就的自我感動上嗎?」
大幅的宣傳廣告與精緻的套房樣間合力向大眾兜售關於未來居所的綺麗幻夢;然而在繁華表像之下,居民的真實居住需求卻在盲目跟風和商業利益的裹挾中遭到忽視。蔡國傑意圖喚醒被物質誘惑蒙蔽的人們要在現代社會的複雜現實中保持冷靜,精準辨別自身真實的居住訴求,回歸對生活本質意義的探尋。

《安居地》展覽是蔡國傑藝術實踐與地產博覽會的一次跨界嘗試,隱晦地利用既有規則進行反擊。在第一展廳的「好風光」項目中,蔡國傑製作了新的「澳門八景」,隨著積水漸幹,地籍格之間隱匿的誤差線跡逐漸變深、波動變大,恰似城市發展背後那些被忽視的細微裂縫,顯露出城市規劃與現實居住空間之間的矛盾張力。蔡國傑對城市發展主導權的歸屬提出質疑:怎樣的城市規劃才能切實為市民營造真正的「好風光」?政府出臺的規劃報告能否與市民對優質生活環境的嚮往相契合,為城市勾勒出理想藍圖?想想路氹連貫公路「金光大道」上博彩企業的奢華建築群,普通市民從中能收穫幾分愜意?實則不過是資本巨鱷們的專屬「好風光」。

移步至《安居地》的「有庫存」項目,蔡國傑以澳門填海造陸的歷史進程為靈感契機,挖掘城市土地利用背後的深層社會心理。歷經三百餘年的填海擴土,澳門土地面積大幅增長,「土地庫存」的概念對民眾而言滋出為一種對填海造陸既熟悉又盲目、對生存資源既緊張又浪費的心態。在此背景下,蔡國傑以「新城F 區」為虛擬藍本,展開了烏托邦式的虛擬城市規劃實驗。他規劃了這座藝術島嶼的藝術空間使用、表述對藝術場地的理解,以鳥瞰、平視等個角度做出了模擬的實景圖,精心規劃島上的樓群和植被,進而呈現出這座虛擬島在白雲藍海之間的「照片」,仿若世外桃源般安靜自處。他還製作出海島模型,邀請市民觀眾插上代表「土地所有權」的小紅旗,將東方人骨子裡對土地的眷戀與依存關係具象化呈現,以反思對城市土地的利用模式,觸探都市人群心靈深處對生活環境的渴望與理想。
澳門著名建築師馬若龍的參與,為《安居地》注入了專業視角。與蔡國傑關注住民意願的藝術追求相呼應,馬若龍強調建築靈魂的重要性,認為建築應承載文化、藝術、科技等多元價值,契合居民生活方式與傳統。他所提供的城市規劃手稿及成果圖,在「投入城市規劃發展的原文化局長個人成果」專案單元中串聯起過去與當下、個人與當局之間關於城市發展的對話。「城市發展場勘團」項目更是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蔡國傑攜手前澳門博物館館長陳迎憲,引領市民漫步澳門街頭巷尾,探尋古城遺跡。「城市是不能『詳細』走動的,問題會顯現」;陳迎憲對澳門歷史故事的娓娓道來,喚醒市民對城市文化根脈的記憶,每一厘土地都鐫刻了往昔歲月紛爭的痕跡,意識到城市絕非冰冷的建築堆砌,而是鮮活的群體生存歷史長卷。

「+1」(板橋,2020)項目則聚焦於蔡國傑母校周邊因歷史遺留問題而陷入土地權屬困境的居民群落。這片承載著幾代人生活記憶的聚居地,由於早期產權登記缺失,在城市擴張、地價飆升的浪潮中,陷入居民與學校之間複雜的利益糾葛。蔡國傑以藝術家的擔當介入其中,在依循當地政務規範征得校方許可後,邀請專業地政事務所進行精準測繪,繪製出真實反映居住現狀的地籍圖。這一專案的展開過程使制度認知與現實土地所有權之間的誤差突顯,反映出不同利益主體因身份差異而產生的認知錯位。以「界限管理師」的身份,蔡國傑憑藉對土地政策的熟稔、對居民心態的共情,以 5 分 14 秒的影像記錄將隱藏在城市視野平和表象之下的矛盾衝突坦然呈現於公眾視野,引發觀眾對城市土地管理公正性與人文關懷缺失的深刻反思。
並未止步於城市宏觀規劃與群體權益範疇,蔡國傑的藝術視野還滲入到居民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契約」(澳門,2022)項目中,他化身理想生活的見證者與引導者,現場為觀眾書寫一對一的「自諾契約」。通過這樣的儀式性行為,藝術家介入觀眾的微觀個體敘事,助力他們珍視自我,以悄然之力重塑人與自身、人與他人的關係範式,讓城市生活盈溢人文暖流。而「你好!上海居民」(上海,2023)項目則聚焦上海流浪居民,邀請他們入住臨時居所,參與藝術創作,共同探索「共用、共創」的居住新模式。蔡國傑希望自己在當代都市的文化熔爐中,給予城市邊緣群體充分的話語權,挖掘「居」與「民」之間相互依存、彼此促進的內在意義。
蔡國傑以作品專案施行對固有土地分配機制的抵抗,拓展城市住民社會參與和訴求表達的管道。他期待自己的藝術創作能夠剖析城市發展進程中隱匿的痛點盲點,探察當代空間權力體系的罅穴,解構再重新詮釋體制規則,憑藉藝術獨有的感染力與創造力,構建起協同共生的邊界政治策略。
2.3 自然與人文交織
蔡國傑的藝術思辨延伸至空間權力結構下自然與人文的複雜關聯。相較於城市,村莊裡人們與土地親近有加。大自然借山脈、水系勾勒出威嚴的空間邊界,在此情境下,人類建造居住空間仿佛是在向地球求食乞憐。從圈地行為的發生到自然資源分配格局的形成,蔡國傑切入對環境正義的討論,剖析人類對自然的功利性利用及社會生態問題。
被稱作「整個村子都是美術館」的甘肅石節子,蔡國傑駐地開展了「識域的邊境表述協議」專案(2020)。當與村民們討論這個自然村莊的邊界時,蔡國傑發現他們心中有著對村莊不嚴謹卻獨特的地理認知——東山谷、南溪水、西岔路、北山梯牆構成了群體概念中的「我們村「。這些模糊而富有詩意的邊界反映了村民對土地和自然環境的情感聯繫。他們在長期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空間感知方式,既不同於現代城市規劃中精確測量的地籍圖,也不等於傳統農業社會中基於生產和生活的經驗性邊界劃分。
蔡國傑捕捉到這一介於明確與含混之間的邊界特質,將其視為對抗現代社會標準化和同質化傾向的文化表達。邊界的含糊不清同樣是當代藝術中對固定定義和分類體系的挑戰;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共鳴: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鄉村生活,都試圖突破既定框架,探索更加靈活多變的存在形式。於此所思,蔡國傑將地界山體牆進行 3D 掃描製作成雕塑,以技術手段使村莊邊界誤差具象化,讓石節子村莊的文化記憶和社會關係呈現為可感實體。

當問及村民們這座藝術品放在村中的哪裡合適時,他們一致認為應該放置於村長家中,「村長最辛苦」,村民對村長的信任和依賴,映現著鄉村社會中的淳樸價值觀及其權力結構。村長作為村莊的象徵性代表,其住所成為了在相對封閉自足的小型社區中連接個體與群體、私人與公共的重要節點;個人角色和集體利益之間微妙平衡,認可並遵循既有的人際秩序。
這場在鄉村展開的藝術介入,通過對石節子村莊邊界的重新詮釋,蔡國傑導向了對群居生活模式中人與自然、過往與當下、個人與集體之間多維關係的思考,邊界並非只是物理意義上的分隔線,而是包含了歷史、文化、情感等多個層面的複雜結構,根植于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念。
在蘇州胥口的「拓寬邊界 30 公分」(2023)項目中,蔡國傑與村民一同壘起冰牆的行為既隱喻了土地邊界與身份政治的關係,也是對物質層面邊界的拓展與消失的象徵。隨著冰牆逐漸消融,在挑戰變動既定邊界的同時,標示著村民身份認同和歷史關係的重構與融合。「平水碑」項目(2020)則關注到了寧波韓嶺月湖裡中不同歷史時期修建的「水則碑」之間的測量誤差。蔡國傑計算出這些誤差並製作了相應的發泡聚苯乙烯的長方體積模型,意圖讓以往僅能透過想像的誤差漂移於並佔據真實水體空間。然而在備展過程中,誤差實體及其說明碑的外觀及位置引起了居民的好奇、關注直至討論和反對,這一串未曾料及的戲劇性波折暴露了古今居民對於「水則標識物」的認知差異,以及藝術實踐與當地居民接受度之間的距離。


蔡國傑還深入探索了人工參與下的自然改造現象,尤其是城市化進程對地理形態的影響。例如在澳門西灣湖邊展開的「22°11’03.6」N 113°32’05.8「E」項目。他每天收集城市塵土並在該特定座標地點進行一個人的填海行動;看似微
不足道的行為日積月累,如古訓「愚公移山」般嘗試以人類活動改變地球表面。撒入塵土象徵著城市發展中的微小活動,當隨著時間推移,終於高出於水面即宣告了陸地海岸線的成功擴張,這一以自然與人為力量交錯作用下形成「誤差空間「的實驗,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邊界-中心「的權力關係及其背後的複雜性。
此外,在杭州「可以分配好的善意水電工程」(2022)和基隆「制度之外:雨水充電樁」(2024)項目中,蔡國傑將目光投向了「無屬的自由資源」——雨水。基隆是一個多雨的城市,年降雨量豐富,但這些雨水在未落地之前並不屬於任何個人或組織。他為這番思緒設計了一座能夠捕捉空中雨水並將其轉化為電能的裝置。觀眾可以在展覽現場用該裝置為手機充電,螢幕上會顯示即時發電量的資料和充電消耗情況;雨水轉化為電能的過程得以直觀展現並被感受,引發對展覽《鏡像回歸:時間光錐》「可以分配好的善意水電工程」專案(杭州·浙江美術館,2022)自然與技術之間互動的思考。蔡國傑認為,雨水在落地之前處於制度的邊緣地帶,具有天然的平等屬性;通過對雨水的收集利用,他提出在資源權屬和分配制度局限性,試圖尋找更為公平合理替代方案,審視社會人類處於自然世界中的生存平衡。


三、省思重構:以藝術撬動秩序變革
藝術在當代社會繁雜多元的語境下已超脫傳統審美範疇的拘囿,為激發公共探討、驅動社會變革注入活力。蔡國傑將藝術與社會議題緊密交合,以獨具一格的藝術語言介入社會。他受列斐伏爾「空間是社會關係及結構的外在映射「這一理論啟發,探究在權力架構作用下空間呈現的當代樣態,憑藉聚焦土地測量誤差及間性空間的諸多作品專案,衝擊傳統土地權屬界定模式。與此同時,他著重挖掘文化混雜在社會構建進程中的關鍵意義,展現實體與意識空間交織的複雜質性,像一面對公眾折射出社會更多潛在可能的棱鏡,悄然推動既有社會秩序的優化與革新。
3.1 藝術實踐的社會介入與空間拓維
蔡國傑認為,藝術與社會依存共生,藝術家自社會生活中構築自己的精神現場,以想像力織入社會議題,才能創作出有趣的作品。他剖析城市空間的藝術實踐,闡說物質表像背後的權力關係與社會結構緊密纏繞的深層網路,以此觸動大眾反思意識形態籠罩下現代化城市的諸多弊病。通過聯合社會群眾進行「空間探討」,對都市制度誤差生成的藝術空間展開新體制實驗——《半田計畫》,蔡國傑意在觸及公眾的關注點,激發關於空間爭議的集體討論,從而在藝術世界中構建持續演進的開放性對話平臺。
《半田計畫》融合繪畫、雕塑、裝置、影像及公共互動等豐富多樣的形式,是蔡國傑基於對藝術家身份的深度認同,針對城市空間、土地使用以及社區參與等重要議題所展開的反思與深度介入之舉。作為「半田計畫」的序章,《地籍圖像志——誤差花署》(2019)繪畫作品以積水使地籍圖原空間邊界的錯位具象化,展現那些被忽視卻具有彈性的間性空間。
常規土地管理規劃常漠視測量誤差,蔡國傑卻從中敏銳捕捉藝術與社會議題的契合點。自商售地籍線系列專案起,他以誤差為簽訂權屬契約的對象,開啟對邊界空間的持續深化探索,並將其作為創作的核心媒材。他將不同時期測量制度重疊的間性空間實例進行實體化,將誤差的正負空間創作為「誤差填充」、「誤差紀念碑」(2019)雕塑,使第三空間介入第一空間。對澳門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區地籍線進行考察,以制度誤差作為城市年輪,掃描出詳實的空間資料記入作為檔案,成為「地籍制度誤差的界域軌範」檔案(「誤差疊置」專案,2021),又借助虛擬實境技術,進一步以「誤差塢堡」(2022)在虛擬空間中呈現形成對新維度空間的介入。

在與「誤差」相關的展場中,他通常會陳列諸多對象地地圖、地籍圖、城市展覽《安居地》「誤差紀念碑」項目(澳門·東方基金會,2019)社區地圖以及各類建築物等資料,同時結合由「半田計畫局」所開展的調研成果、法定文書以及簽售合同等素材。此外,他還會在現場設置簽售辦事桌,親自或委託經授權的房產經紀人向觀眾詳盡介紹簽售物件及相應的買賣規則,並且在尊重觀眾意願的前提下促成真實的合同簽署與金錢交易行為。
在那些對其意圖不甚瞭解的人看來,這似乎是藝術家用「藝術概念」針對觀眾真實財產所進行的一場「空手套白狼」式的過家家。然而,當雙方都清晰知曉遊戲規則時,這場周瑜打黃蓋式的奇特交易行為實則坦然得毫無隱晦之處。正是這種藝術實踐所蘊含的荒誕感和戲謔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進而推動旁觀者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被售賣的土地究竟源自何處?答案即關切到對土地地籍圖的「測量誤差」這一概念的闡釋。藝術家是否有權出售這些土地?這一問題又促使人們反思土地資源權屬規則制度制定的合理性。
藝術家宣稱因發現「誤差」土地而獲得了所有權及售賣資質,這是否可被視為當代社會及概念層面的新「圈地運動」?在這一系列問題的持續追問與推進過程中,思考逐步走向深刻,指向了「對權力的偵辨」和「資源/權力的再分配」,以此推動「平權驅動」進程,消解權力的制度慣性,促使藝術的公共性實現轉變,即從單純的作品展示演變為實踐專案發起者向社會公眾發出的參與邀請,引領公眾共同成為思考更為宏大社會議題的「局外」觀察者。
當代藝術積極介入社會現實,引發公眾對各類問題的關注思考。蔡國傑從對土地誤差的洞察與反思入手,促使人們重思權力、制度、公平等概念的內在關聯與複雜性。他聚焦城市發展中的利益博弈,借藝術話語言說制度漏洞,進而叩問人們為何會輕易認同並陷入權謀的既定規則體系之中。通過藝術呈現土地「間性空間」,蔡國傑引導公眾質疑人為邊界,撼動既有制度信任根基,覺察隱匿的權力運作。他繼而將土地分界邏輯映射至社會人群分化,引導習慣被區隔的大眾反思處境與關係,去聚合因權力撕扯而分散的力量,促進地界、人群與城市相融共生,拓展無階級、無邊界的藝術空間。
3.2 藝術驅動的制度反思與重構探索
在當代藝術的多元生態中,蔡國傑的藝術實踐如同光照現有社會和政治制度深層肌理的無影燈,既滿溢人文溫情,又攜冷峻理性,柔和卻不容回避地將隱匿於制度背後的權力架構,以及驅動其運作的內在機制展露無遺,探討如何雕琢社會空間,左右個體命運軌跡。他以藝術剝開制度外殼,喚醒人們對其內核的省悟,思索後續制度的蛻變、重構摸索前行的方向,探尋潛在的可能路徑。
從簽售間性空間,到試圖以售賣地籍線款項集資購置「獻給自由」之土地,蔡國傑回溯土地測量與權屬界定根源,挖掘制度圍裹下的社會權力關係。在歷史演進的土地劃分進程中,人為制度因素貫穿始終;測量技術的選用、標準設定和土地權屬的敲定,無一不受制度左右。蔡國傑思考制度因素對資源配置格局的作用,將畸零地視作未被「收編」群體在社會與自然生態中的象徵,討論其對社會結構、個體生存的深層影響。制度或顯或隱性地使優質資源偏向少數利益集團,這一傾斜悄然埋下社會階層分化與矛盾激化的火線。蔡國傑在如《安居地》展覽等系列專案中有意聚焦土地開發規劃議題,觀察制度在空間分配和資源管控方面衍生的亂象,將權力機關、開發商等各方圍繞土地資源的利益角逐、權力操弄等博弈呈現於眾,喚起公眾對權力制度的感知與深入探討。

在城市化的迅猛進程中,制度主導的規劃路徑大多執著於宏觀經濟資料的攀升以及城市光鮮外表的雕琢,卻將個體切身訴求與空間分配的公平正義束之高閣。蔡國傑以對間性空間的關注和創作切入藝術語境中的「權力場」,在宏觀城市發展與個體權益保障之間找尋平衡,成為理想社會空間構建與追求之路上的同行者。
儘管打造絕對平權社會空間的理想如海市蜃樓,蔡國傑仍執著於借藝術撬動制度縫隙。他設想整合以往簽售專案所獲資金,並聯合部分人士購置一塊土地,打造「釘子戶」模式(通過設置需全體聯名者簽署才能轉售的規則以增加轉售難度,以買賣行為制衡買賣),這一在與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財務主任交流並獲得支持後逐步推進的構想,被命名為「獻給自由」(籌備中),打破現有社會制度與權力的束縛,構建更為公平、包容的社會空間及運行框架。「自由之地」裡,人造邊界的界限權力與欲望充分暴露使人們啟動內心深處對自由的渴望,消解物理實在與人群內部的「畸零地」,平衡地塊和人群之間匱乏與不均,讓無產者也成為「地主」式的資源擁有者,實現權力與資本的流轉共用。
蔡國傑認為,藝術家有責任不斷尋找再思的空間,再堅固的系統也存在誤差,邊界之處往往藏有權力結構鬆動的契機。在「以土地之名「專案(2024)中,他轉變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藝術追問形式。經過實地走訪調查澳門的土地信仰,他由對「家園「的追尋延展至對神明的請示,設計了一套藝術行為規則,邀請觀眾為新土地命名。

「舊空間」的觀眾憑藉自身生活經驗與內心祈願為「新土地」命名,通過擲筊儀式向土地守護神明請示所擬之名的認可與否。蔡國傑設定以擲筊者中笑杯出現次數最多的命名為勝,而笑杯的「雙陽」在通常語境往往意寓順平,于擲筊時卻表示不明確,需重新擲筊以獲確切結果。這一現象側面引發對「聖杯」(一平一凸)作為神明默許象徵的思考,指向陰陽平衡、矛盾對立才為恒常的古人智慧。展覽結束時,集名箱的破裂仿佛冥冥中真有神靈欣然接納了這種眾人對借由科技之力創造的新土地所寄予的期許。這一過程中似乎在印證利他之心對業力阻礙的化解,在純粹願力的驅動下形成了深度的能量連接,民眾與土地間那條直接、穩固且親密的紐帶再度浮現,土地由此重新回歸民眾的情感與精神世界。

蔡國傑以其嬉笑之下的嚴謹態度梳理關於制度的思考檔案,讓自己保持對都市生活的距離,以觀察者的冷靜審視社會議題。通過詮釋都市制度誤差,他挖掘制度自身所產生的間性空間,並基於對「第三空間」理論的延伸將其轉化為自己的藝術生成方法,嘗試以藝術實踐探索構建新的秩序空間。在「誤差塢堡」(重慶,2024)中,蔡國傑借助現代技術超越了對受限的現實物理空間的類比複刻。通過細緻對照調研澳門不同歷史時期與現代的地籍圖,他收集了地籍線變化、建築遺址疊置的豐富證明,這些「城市年輪」般的歷史痕跡見證了地方權力的變遷歷史。在精確測量、掃描並建檔後,蔡國傑將誤差填充製作成紀念性空間實體,展覽《何以閃爍——四川美術學院與大灣區新媒體青年藝術家邀請展》並切割成數段傾斜放置于展場,佈置出觀眾可以穿行其中的空間;再利用 VR 技術將制度自身所產生的空間詮釋生成「塢堡實體「,為處於制度誤差困境中的觀眾提供一處借助技術設備暫時逃離現實制度枷鎖的棲息之所,在虛擬世界中真切地領略自由。這一專案拓展了藝術介入制度批判的維度,顯現了藝術在社會制度變革進程中的潛在能量。

結語
自萌生對誤差空間的關注意識起,蔡國傑在二十年的藝術實踐中審慎地剖析土地背後隱匿的權力架構,衝擊傳統權屬認知,促使人們省思土地制度的合理性。在人文關懷向度下,他聚焦邊緣群體,從家園記憶、城市住民訴求到自然與民生的交匯,為弱勢群體鋪設表達通路,傳達出城市發展中被忽視的公眾意願,探尋人與自然的共生新機。他進而以藝術為杠杆,介入社會秩序邏輯,驅動制度反思與重構,在荒誕戲謔的藝術表達中,聚焦權力運作與資源配置,尋找構建公平、包容的社會空間可能路徑。如同置身複雜飯局的清醒斟酒者,蔡國傑執著於在制度罅隙間傾灌作品佳釀,引動公眾透視社會幽微,咂摸權力、空間與群體關係的辛辣醇香。
撰文 | 趙願
編輯 | 樊婉貞
圖片 | 藝術家提供
《潮壤相接》 | 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期 | 2024.12.14 - 2025.04.20
展場 | 本館 104-105展覽室
——— 探索更多藝術地圖 ———
資訊投稿 |editorial@artmap.com.hk
@artmap_artplus
@artplus_plus
@ampost_art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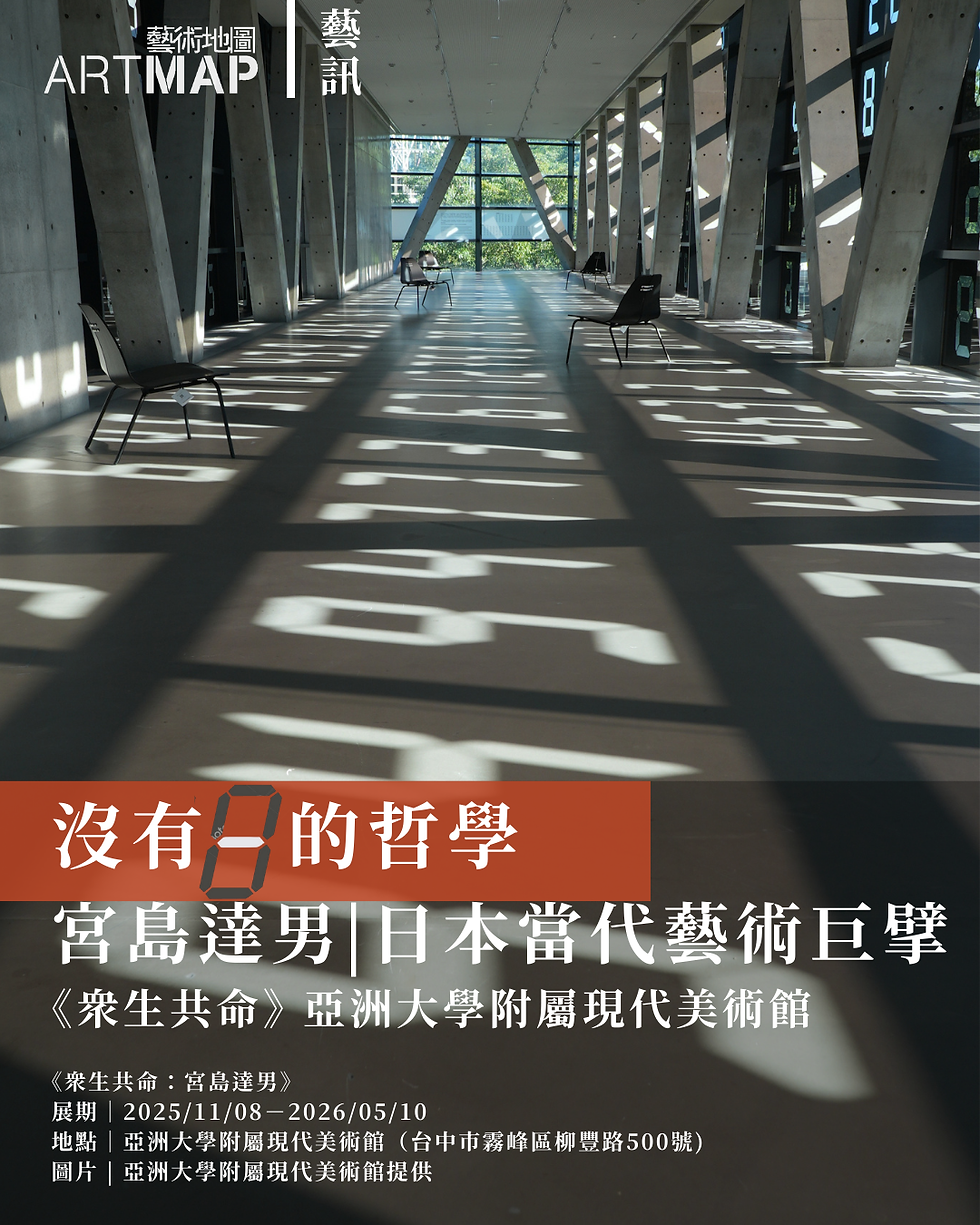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