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評論家 | 套用神話發明學 重構歷史景觀 | 塘西無風月 | 香港話劇團
- experience am space

- 6月25日
- 讀畢需時 6 分鐘
已更新:6月30日

《塘》是潘惠森最新的劇作,延續其過去隱晦的風格,笑鬧之餘,又存有廣博的解讀空間和可能。在場刊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幅創作腦圖,和關於「重創」(即在羊皮紙上刮去文字重新寫作,亦代指具有多種意義、風格的事物)的簡介。
「馴悍記」出自莎士比亞的同名劇作,講述一個貴族捉弄街邊喝醉酒的補鍋匠斯賴,斯賴醒來後被告知他是已瘋癲多年的貴族老爺,隨後為醉漢表演的劇中劇,才是《馴悍記》的主體:即一眾追求者求娶溫順的比安卡和難馴的凱瑟麗娜姊妹,最後潑婦被馴服為一個忠順的妻子的戲。《馴悍記》(《The shrew》)是莎士比亞早期的喜劇之一。
潘惠森儘管擅於從古今中外名著中取材化入劇本,但本劇與《馴悍記》劇情本身殊少關聯,我們不妨單從字面意思理解「馴悍」二字,把這種抽離原有脈胳的挪用視作劇本(或者說,「重創」)的注腳之一。

| 塘西無風月—重創的景觀
提起塘西,很難不聯想起《胭脂扣》的如花和十二少,還有燈紅酒綠的塘西風月、乾煎石班,本劇卻刻意迴避了大家熟知的想像,把時間設定在1935年香港全面禁娼後,石塘咀煙花不再,只剩下一間「塘西大酒家」在苦苦支撐,老闆孫二娘(小名Lin,即凱瑟麗娜的「麗」)和手下四女(毛毛、紫菜、蘭花、小菊),為了爭取僅餘的四個客人和最後埋街食井水的機會,積極轉型求生,搬出歌舞表演和按摩服務,卻因為以砂鍋拔罐燒傷了四男(大帥、經理、少爺、跟班),由是引出後面四男尋仇、追求五女以求寶藏線索、被反將一軍的情節。
當那些香艷或浪漫的想像被1935年的全面禁娼刮去,「塘西」的內涵便被重新書寫,老鴇-妓女-恩客的敍事被打破,塘西大酒家比起男性尋歡享樂的場所,更像孫二娘和四女的家,是一群底層女性抱團取暖掙扎求存之所,而四男也失去了本來居高臨下的恩客身分,以一種或可笑或無能或真摯的姿態,與五女交互拉扯。

我們不妨先檢視各人的生存狀態,再進入他們之間的互動。
孫二娘幼時跟隨賣腸粉的父親來港,多年打併,才有了大酒家的產業,四女也是窮苦人家出身,被孫二娘收留,儘管她們的身份是塘西阿姑,主要展現的特質卻是憑自己努力打拼的堅韌,並不依靠男性的垂憐,也無法被「馴化」,只是時運不濟,全面禁娼後生計頓失,不知何去何從,只有努力求變,見步行步。
四個男人(大帥、經理、二世祖、跟班),固然有他們各自的風格和特性,整體卻是追求權力而不擁有權力的人。大帥自稱曾經在某段時間參加北伐,射過大炮,事實是北伐結束早於他宣稱的時間,多半是在「車大炮」;經理的營生依靠碼頭的航運業,在全球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其營生也無甚保障;二世祖的財力自然依賴父母,跟班也自然是二世祖的下游。
四男一開始光顧塘西大酒家,是為瞭解悶,這種悶除了百無了賴的沉悶,也隱隱指向四男無法展現男子氣概的苦悶,所以他們試圖證明自己才是四男中較優越者,也為了滿足色欲而光顧酒家,最終四男被燒傷送院後回來尋仇,五女也是利用他們自己的色欲退敵。
而四男之所以對張寶仔的寶藏產生興趣,也可以理解為希望得到寶藏帶來的權力,擺脫無權的狀態,在追求五女以圖歌謠線索的過程也是馴化她們,使她們順服的嘗試,而五女也同樣地利用四男的欲望欲拒還迎,更把歌謠線索導向不停被改寫的市井八卦,使四男一無所獲。
最終當五女山窮水盡,被四男圍困在酒家內,則反過來穿上男裝假扮員警,要以嫖娼罪(五女正是因為禁娼而陷入一開始的困境!)抓捕四男,因而反客為主,成為制宰四男的上位者。
在這條故事線中最有趣的點,正正是四男一切為了得到權力和佔據上風的行為都只使他們吃了更多的虧,他們試圖馴化五女的過程同時也是被五女利用欲望馴化的過程,男性-女性,妓女-恩客間的權力關係被全然巔覆。

| 張保仔寶藏—神話發明學
在劇情開始前的旁白說過一句頗堪玩味的說話,「這是一段虛構的歷史,虛構的人物,真實的故事。」
張保仔的寶藏到底藏在哪裡?跟歌謠又有甚麼關係?筆者以為寶藏除了是推動劇情發展的工具,同時也是在隱喻神話、傳說,那些存在於我們共同想像中的概念和故事,寶藏有多少,確切是甚麼,最後有沒有人找到,並不重要,因為它只是對劇中使用的各種文化符號(塘西、南音、通勝英語、張保仔傳說、在1935年的香港根本尚未成名的張愛玲)的一個總喻。
關於寶藏的故事和它所承載的意義,就和歌謠和市井八卦一樣,是在被口口相傳(以訛傳訛)的過程中層層累加地創造,至於張保仔其中作為海上一霸或俠盜的生平,作為被清廷招安討伐其他海盜的武官,作為清帝國邊陲歷史的一部分,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就跟這個1935年的塘西一樣,被完全刮去了原有的文字重新書寫,變成寶藏前一個空白的前綴,一種想像。
張保仔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傳說不停被重新創作的過程,穿膠花的誠哥和他的煉金術,又會是甚麼呢?在這個1935的香港,是不停被重新詮釋的獅子山下精神?是「知識改變命運」嗎?還是遠在1935年後,真正堪稱點石成金的房地產業和高地價政策?劇裡固然沒有明確的說法,只是留給我們無垠的想像空間。
劇中的歷史固然是虛構,卻總是隱隱指向真實的故事,無論是兩性間的權力關係,被蕭條年代碾過頓失所依的人們,南下香港白手興家努力生存的市民,乃至於這些被抽空又填滿的符號。

| 說故事的人們
關於「說故事」這件事,劇中對時代背景刻意模糊處理,雖然交代了1935年的時代背景,卻刻意在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政治格局、全球經濟蕭條等宏大視角時語焉不詳,故事雖然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以後,所指向的時間,卻不限於1935年前後,那部播放歷史背景的投影機,斷斷續續的,虛虛實實,彼時彼刻,又怎麼不能是此時此刻?虛構的歷史,又如何不能指向真實的事件?
在故事的主體以外,還有說書人和樂師兩個不停穿插的角色,他們構成了另一條較為隱晦的故事線,樂師一開始向說書人求取工作機會,跟說書人擔任同樣的旁白角色,同時還加入了配樂,但卻慢慢佔據了說書人原來的位置,搶了他的飯碗,連叫家鄉雞也只給他留雞屁股,而樂師比起說書人,更慣於以敍事者/旁白的身分打斷主線的敍述,甚至刪改孫二娘父親遺下的錦囊,二娘每唸一句他就刪一句,這個說故事的人,漸漸以他的意志,影響故事的內容。

我們不妨把說書人和樂師,視為兩個在爭奪故事詮釋權的人,而說故事本身就是一個重新創作、重新發明的過程,這個1935年的香港故事,就是被重新發明的塘西、南音、通勝英語、張保仔、煉金術構成的想像,樂師漸漸開始更為進取地修改孫二娘的生命經驗和她父親的故事,只是這個過程的一次濃縮體現。
(自此,我們得以窺見這部嬉笑胡鬧的塘西馴悍記,謎面背後環環相扣的各種意圖,像一個有待探索的精密的迷宮,而筆者對這個謎語的解釋,又何嘗不是在重新敍述這個故事?)
文 | 鴿子全
圖 | 香港話劇團
《塘西馴悍記》|香港話劇團
觀看地點 | 香港大會堂劇院
觀看日期 | 24.06.2025
——— 探索更多藝術地圖 ———
資訊投稿 |editorial@artmap.com.hk
@artmap_artplus
@artplus_plus
@ampost_artmap
西無風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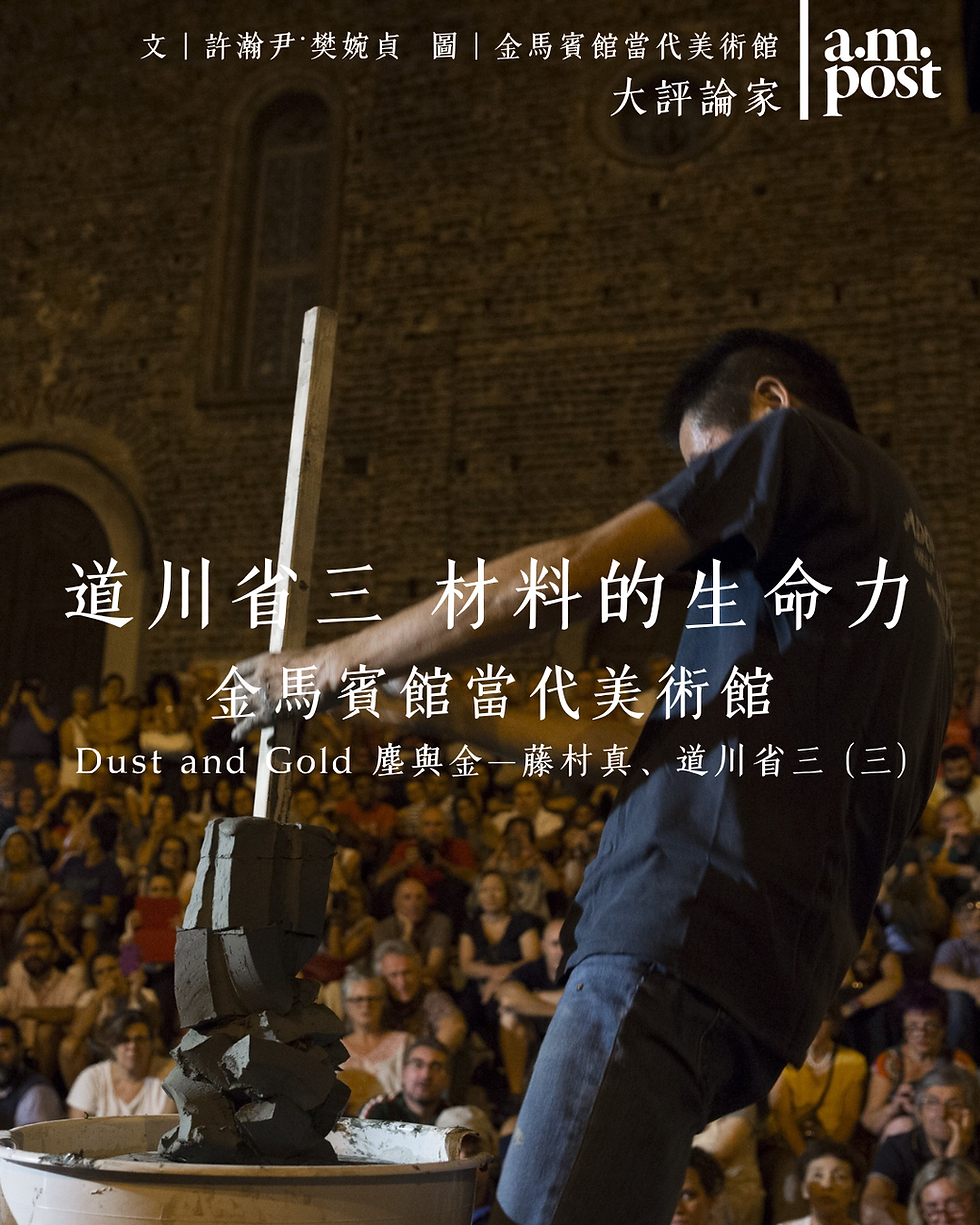
留言